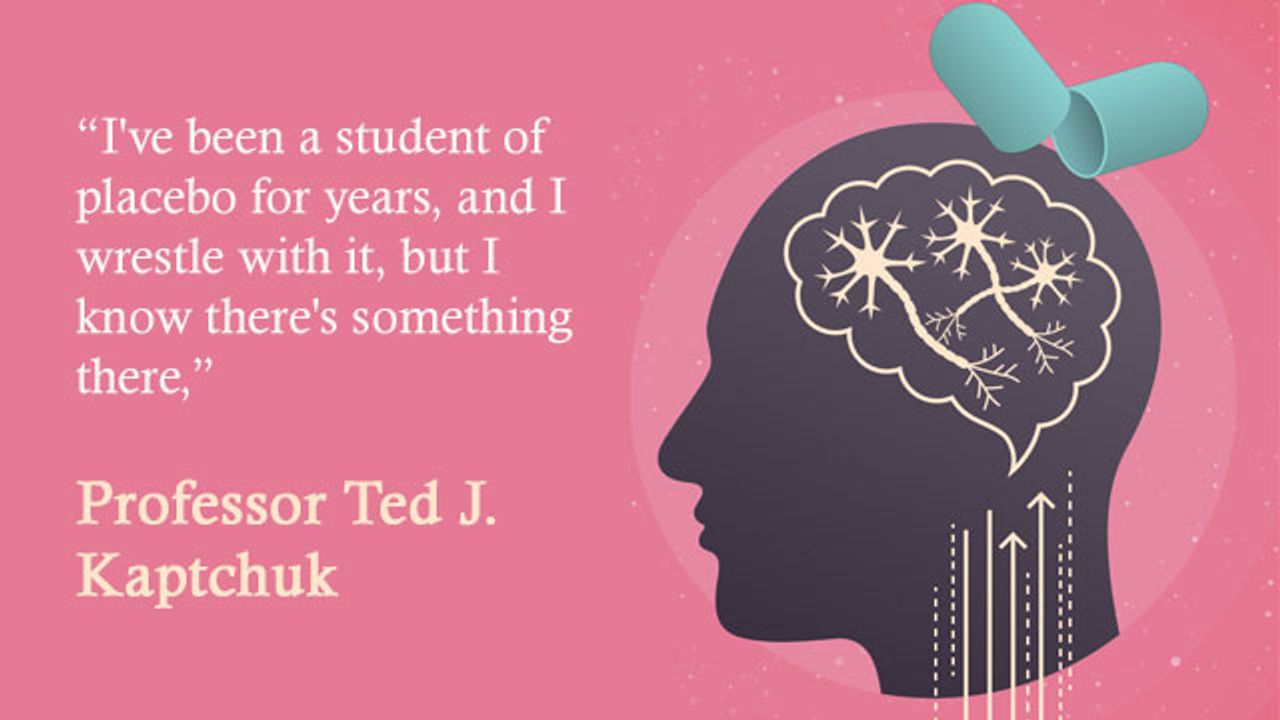
这Placebo Response ‒ A Powerful Phenomenon

这Placebo Response ‒ A Powerful Phenomenon
填写下面的表格,我们将向您发送PDF版本的电子邮件“安慰剂反应 - 一种强大的现象”
1807年,在给卡斯帕·韦斯塔尔博士的信中,托马斯·杰斐逊笔,“我认识的最成功的医生之一向我保证,他使用的是更多的面包药,彩色的彩色水和山核桃灰的粉末,而不是所有其他药物放在一起。”
尽管早期观察到在医学中使用安慰剂和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所记录的益处,但推动这些生理反应的精确机制-或安慰剂效果-仍然难以捉摸。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捷克葡萄牙直播很高兴与Ted J. Kaptchuk教授, leading figure in placebo studies and a scholar of East Asian medicin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humanistic dimensions of care, what is currently known about the neurobiology and genetics of placebo effects, open-label placebo studies and ethical use of placebos in clinical practice.
替代药物的非凡途径
“I was very involved in the antiwar movement in the 1960s, which was impacted by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Vietnam War. But at some point, I realized I had to earn a living. And I thought, why don't I study this weird Chinese stuff?” says Kaptchuk.
在此期间,他为他提供了有关他的生活的一些背景,并解释了一项特定事件如何使他从事替代医学,特别是中医的职业:“纽约市举行了大陪审团的听证会。我被要求作证我的一些朋友,他们离开了深处,真的变得很糟糕。”
但是,他意识到自己不想作证,为了避免这样做,Kaptchuk搬进了旧金山红卫之家。红卫队是一个亚裔美国人组织,于1969年在旧金山的唐人街成立,隶属于黑豹派对,根据Kaptchuk的说法。
“我在那里躲了三个月,在那段时间里,我阅读了中国的国家新闻杂志Peking Review,现在被称为北京评论。在其他所有问题的后页上,有一个故事,其中说过“中医是一件很棒的宝藏”。
他知道他不想从事“常规”职业,而是决定学习亚洲医学。Kaptchuk于1971年前往中国,并在中医研究所学习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中国医生。
当他于1976年回到美国时,卡普楚克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开设了一项小型私人执业。他解释说:“我在私人诊所都练习了很长时间,还在公立医院经营疼痛诊所已有10年了。”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Kaptchuk开始注意到他的一些患者快速进步。“他们(病人)会以我写的处方走出我的办公室。但是他们看起来像是在走出去时看起来好多了,步态很乐观,看上去更加充满活力。” Kaptchuk指出。
这让他感到困惑,这是怎么回事?“我只是坚持这个问题。直到我被招募到哈佛医学院进行替代医学研究之前,我才真正追求它。”
Making the switch to placebo studies
为了准备搬到哈佛大学,Kaptchuk开始与统计学家和流行病学家学习。“我有机会问一个伟大的20Th世纪统计学家,弗雷德里克·莫斯特勒(Fredrick Mosteller),谁是我的伟大导师和英雄之一,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 我的工作将是什么?”
事实证明,kaptchuk的工作是找出是否替代疗法不仅仅是安慰剂效果。但是首先,他本人需要准确地了解“安慰剂效应”一词的含义,所以Kaptchuk问他的导师:“他说,它[安慰剂效应]是惰性物质的效果-我心想‘不要说什么,但这是一个矛盾的-无效的物质的影响?’。因此,我开始怀疑我是否应该研究安慰剂效果而不是替代药物,因为没人对此一无所知。”
Kaptchuk切换了重点,并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提交了一些关于安慰剂效果的赠款,这些申请获得了批准,他的工作得到了大量资金。
Kaptchuk说:“那时候我开始了一名安慰剂研究员的职业生涯。”
Clearly unsatisfied by his colleague’s definition of the term, I asked Kaptchuk how他会描述安慰剂效应:
“我要说的是,安慰剂效应是患者有时会因浸入临床相互作用而获得的积极好处。它与仪式,符号,单词,沉默和发生的行为有关。”
He adds,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exact mechanisms are, because I think there's much more work to be done. What I’ve provided is a descriptive explanation, which I think is accurate. Although my colleagues don't like it, because they think they already know how placebo effects work.”
安慰剂医学和护理的人文层面的价值
在2008年,Kaptchuk等人。出版学习在BMJ探索安慰剂效果是否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以及在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中,是否可以重新组合这些成分以产生症状的增量改善(n = 262)。审判参与者被随机分为三组:
- 第一组:仅评估和观察
- 第二组:治疗仪式(评估,加上截短患者的安慰剂治疗-从业者互动)
- 第三组:支持患者-从业者关系。仪式(评估,加上订婚患者的安慰剂治疗-从业者互动)
“足够的救济”在第一组中最低,在第二组中最高,在第三组中最高。为期六周的试验表明,安慰剂可以为患者提供比时间本身更多的治疗益处(无治疗),但是当安慰剂与参与的患者结合在一起时-从业者的互动,这有很大的浮雕。
误以为蛇
大脑可以用作预测机,这是Kaptchuk在他的过程中详细讨论的Tedmed Talk2014年。他向我提供了“棍子”的例子:“您在森林里,您在走路,您知道森林到处都是蛇。你看到一个长长的对象-your brain’s visual processing will see that object as a snake, even though it’s a stick.”
Anticipatory mechanisms are critical for human survival, explains Kaptchuk, and while his snake/stick analogy is easy to digest, he shares a more relevant example in the context of placebo: “When a person feels sick and down and they go into an environment that is designed to help them and the people in that environment想to help you and have access to the kinds of technology or treatments that society has to make them feel better, the brain’s processing of sensations, of self-awareness and symptom changes – sometimes in a very positive way.”
Kaptchuk强调了他所描述的“标志性实验”,该研究人员由温哥华的研究人员进行,并在ScienceThat demonstrates the point above. The team sought to determine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placebo response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The study involved six participants that were all initially on a stable dose oflevodopa-多巴胺的前体用作多巴胺替代剂。所有六个都是然后服用n这种药物,导致大脑中多巴胺水平降低。他们的症状恶化。
Kaptchuk指出:“多巴胺在帕金森氏症的颤抖和僵化的神经元中发挥了作用。”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该团队能够测量和可视化大脑中多巴胺水平的降低。
这participants were then given either placeboorTheir original dose of levodopa. The researchers noted that for those given placebo, there was a “substantial release of endogenous dopamine in the striatum.” This increase in dopamine was equivalent to the levels of dopamine that would be observed if they had been given the stable dose of levodopa.
Kaptchuk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副其实的药房。”
单词的力量
当医生提供处方时,传达给患者的信息被认为在患者对疗法的反应方式中起着作用。为了研究这一假设,Kaptchuk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试图确定是否可以改变偏头痛患者(n = 66)对活性药物(Maxalt(Rizatriptan))的反应方式或安慰剂。他们的发现发表在科学翻译医学。
该小组研究了459次偏头痛攻击。在初次会议中,患者记录了他们的疼痛程度和任何相关症状(偏头痛后30分钟和2.5小时),他们获得了六个包含含有药丸的信封,以便为接下来的六次偏头痛发作中的每一种。
Of these envelopes, two were labeled “Maxalt” (the name of a common migraine drug), two envelopes were labeled “placebo”, and two envelopes labeled “Maxalt or placebo”. The pills supplied to participants were indistinguishable.

当患者被标记为Maxalt时,Kaptchuk解释说,这“可能给了他们救济的期望”,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正在接受活性药物,并且平均而言,个人报告说2.5小时内疼痛减轻了30%。
当给患者的最大标记为安慰剂时,平均患者报告说2.5小时内疼痛减轻了38%。“当患者收到标记为安慰剂的最大值时,他们正在接受药物治疗-but without any positive expectation,”著名的拉米爆发该研究的一位高级作者在有关该研究的新闻稿中。“这是一种试图将Maxalt的药物效应隔离为任何安慰剂效应。”相反,标记为Maxalt的惰性安慰剂是试图将安慰剂作用从药物效应中隔离出来的一种尝试。
When patients were given Maxalt labeled as Maxalt, on average they reported a reduction in pain of 62%.
Kaptchuk说:“尽管Maxalt在缓解疼痛方面优于安慰剂,但我们发现在三个消息或标签中的每一个下,安慰剂效应至少占受试者总体疼痛缓解的50%。”
安慰剂提供缓解,但很少治愈
这positive therapeutic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placebos are not attributed to altered pathophysiology of diseases, rather they are limited to the symptomatic manifestations of the disease. Kaptchuk explains that while a placebo can’t shrink a tumor, it could help to improve symptom management, for example, cancer-related fatigue.
在一篇文章中,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Kaptchuk和美国生物伦理学家富兰克林·G·米勒(Franklin G. Miller),指出:“虽然安慰剂可能会提供缓解,但他们很少治愈”。
Kaptchuk指出:“安慰剂作用主要发生在由自我关注的疾病中发生,医生称之为主观结果,例如疼痛,疲劳,恶心,偏头痛,肠易激综合症等疾病。”
“There’s not one placebo effect. I always try to specify placebo effects, plural. They'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diseases and illnesses. Placebos aren’t only about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mind,涉及神经递质。例如,内啡肽以及内源性阿片类药物,大麻素,多巴胺和5-羟色胺。我们知道,神经生物学机制和脑电路参与了引起安慰剂反应,但显然,那里的复杂性更高。”
Kaptchuk补充说:“实际上,症状管理药物通常模仿身体已经可以做什么,而不是相反。”
尽管我们目前尚不清楚患者如何体验安慰剂效果背后的整个过程,但Kaptchuk解释说:“我们对小难题有很好的了解。”
他继续说:“当人们对安慰剂做出反应时,大脑的某些定量,相关区域就会参与。神经影像可用于突出这些特定领域。”研究表明,包括前扣带回皮层,前岛,前缘,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在内的区域在安慰剂镇痛。
药物基因组学和安慰剂
有新兴数据表明某些遗传多态性可能如Kaptchuk及其同事所指出分子医学趋势。
Kaptchuk说:“我们的团队是第一个找到安慰剂遗传标记的团队,我们处于遗传问题的最前沿。”
在2018年,凯瑟琳·霍尔(Kathryn T. Hall),约瑟夫·洛斯卡佐(Joseph Loscalzo)and Kaptchuk published an article inACS化学神经科学关于对安慰剂反应的基因组影响,他们在较早发表的论文中创造了“安慰剂”分子医学趋势。
霍尔认为,该研究的第一作者说:“安慰剂研究往往是多学科的,很少有遗传学家或计算生物学家有兴趣研究惰性干预措施的影响。甚至更少的资金来源有兴趣冒险回答谁对安慰剂的反应问题。”
To do robust genetic studies Hall emphasizes that you need a lot of participants: “Genetic effects in behavioral outcomes are often small and combinatorial, that is multiple genetic products interact to influence these effects. So early work in this field has relied on secondary analysis of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s for the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and candidate gene analyses of smaller studies.”
这ACS化学神经科学学习sough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genetic variation in the molecules mediating signaling pathways – known to play a role in an individual’s response to placebo – could cause变化性作为回应。霍尔等人。进行了全面的文献综述,并开发了一种算法来研究可能与安慰剂反应相关的基因/蛋白质。由此,他们创建了一部分,这些蛋白质富含神经递质,激素和细胞因子,可以映射到疼痛,自主和免疫安慰剂反应途径。Kaptchuk及其同事发现许多基因/蛋白是已知的药物靶标。
根据对于作者来说,15种药物类别“包括镇痛药,食欲抑制剂和抗抑郁药”,绘制了次数的映射。尚不清楚安慰剂反应途径中的遗传变异如何影响临床研究,但是对安慰剂的进一步研究似乎支持了可以改变治疗反应的假设。
霍尔进一步讨论了这一点:“基因-药物相互作用可以掩盖药物的真实作用(有益或有害)。为了评估临床试验的结果,我们依靠平均值。我们查看药物治疗组中的综合效果,并将其与安慰剂组中的效果进行比较。如果有大量亚群对安慰剂反应但没有药物,并且当我们发现另一个子集与具有反应反应的相同遗传基因座相关的子集,即当我们平均每只手臂的结果时,对药物反应但不反应安慰剂,这些效果被掩盖了。”
Although according to Hall, this is observed time and time again in the literature, few researchers are interested in examining this further. The reason for this, she believes, is that there is a powerful mindset among clinical trialists thatTheir试验将是成功的,“毕竟,他们具有令人信服的和证明的作用机理,安全性,并在小阶段1甚至第二阶段研究中证明了好处。”
“By the time they get to the Phase 3 or even large Phase 2 stage they are not expecting to fail. Why would they do the trial if they really believed they would lose hundreds of thousands – millions of dollars? Then when the trial is completed, the results unmasked, it’s too late,” Hall adds.
她继续说:“底线经常是安慰剂击败他们,在审判结束时为时已晚。次要分析以剖析发生的事情,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事后分析或事后观察只有在您可以返回并进一步检查发现的情况下才有用。
在一个separate出版物霍尔及其同事表明,在儿茶酚-O-甲基转移酶中的某些多态性与对IBS中安慰剂治疗的反应更大的可能性有关。她还对几个大规模随机试验其中包括童年哮喘管理计划(哮喘),妇女基因组健康研究(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cancer).
“我们在每种情况下都观察到的基因-药物/安慰剂相互作用掩盖了药物的真实作用。但是,我们无法重新注册这些试验来研究安慰剂效果,因此这些发现的复制对于向前推动它们至关重要的结果是很慢的。”霍尔总结说。
转移人们对安慰剂的看法
随着围绕安慰剂反应的基本机制的更多证据表现出来,Kaptchuk认为医生对这个想法变得更加满意。但是,该领域的研究在医学界仍然很边缘,因为没有多少群体获得资金。
“我们生活在以药房为中心的医疗界,安慰剂效果确实被欺骗和欺骗的概念所污染。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可以尽一切可能改变这是我的工作,” Kaptchuk说。为了改变人们的看法,Kaptchuk进行了许多“诚实”的开放标签安慰剂研究,从而将安慰剂完全披露给研究参与者。
“我们生活在以药房为中心的医疗界,安慰剂效果确实被欺骗和欺骗的概念所污染,”
在他的职业生涯的早期,Kaptchuk调查了在双盲环境和实验室欺骗的情况下使用安慰剂的使用,但是随着每张发表的论文,他开始越来越感到不安:“我在临床护理中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意味着在临床护理中做不到的事情,这意味着在双盲或类似欺骗的情况下,通过隐藏式安慰剂。”
2010年,Kaptchuk换了齿轮。他不相信安慰剂效应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患者认为他们正在接受活跃的药物,但实际上他们被分配了安慰剂,这就是他们开始感觉更好的原因。
“我的同事安东尼·勒博博士说,‘这是你有史以来最疯狂的主意-但是,让我们去做吧,” Kaptchuk回忆道。通过给予参与者诚实的安慰剂(从每个参与者那里获得了知情同意)并将其数据与无治疗控制进行比较,可以查看诚实的安慰剂是否有效,而无需回归的无治疗控制权(A)可以使重复数据自然变化的统计现象似乎是真正的变化)和自发缓解。
研究开放标签安慰剂的影响
在一个PLOS ONE2010年12月发表的论文,Kaptchuk及其同事分享了单中心,随机和受控的三周研究的结果,旨在调查非欺骗性的,非固定的安慰剂给药(开放标签安慰剂)优于无效治疗控制,80例IBS患者。
这authorsfound that“patients given open-label placebo in the context of a supportive patient-practitioner relationship and a persuasive rationale had clinically meaningful symptom improvement that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a no-treatment control group.”
由于这项IBS试验被认为是首次将开放标签安慰剂与无治疗控制的随机对照试验,Kaptchuk至少又提出了七个非欺骗性安慰剂研究。
Kaptchuk说:“我的目标是诚实利用安慰剂效果,并使它们成为许多由自我关注的功能性疾病的治疗选择,例如慢性疼痛,肠易激综合症,慢性疲劳和更年期的热闪光。”
他继续说:“我不确定是否会被采用,但患者肯定会尝试。例如,那些患有不懈的不适的患者,医生找不到任何理由,高敏性疾病。”
“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试验,数量或参与者更长,以生成更多的数据。但是对于有些不舒服的医生来说,他们被教导开出具有超出安慰剂的药物。” Kaptchuk说。
Kaptchuk和他的团队正在积累证据,表明安慰剂可以在这些类型的患者中诚实有效地使用,而没有副作用。
In 2021, Kaptchuk and colleagues published the results of a larger six-week IBS study (N= 262) in疼痛。“ IBS是进行医疗保健咨询和工作或学校缺勤的最常见原因之一。IBS的有效治疗方案有限,我们假设有可能在道德上利用安慰剂效应以获得临床利益,”said安东尼·莱姆博,医学博士,贝丝以色列执事医学中心医学教授,该研究的对应作者。
“ […]接受开放标签安慰剂的参与者中有69%的参与者报告其症状有意义的改善。”新闻稿。
在一个ddition, those that received the open-label placebo experienced improvement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ose reported by individuals assigned to the no-treatment control arm.
开放标签安慰剂和双盲安慰剂臂之间的症状改善程度没有差异。“这两组之间没有区别的事实令人震惊,没有人可以轻松解释- 但是w帽子关于治愈潜力的有力陈述。” Kaptchuk指出。
负面的期望和Nocebo效应
促进有益或“阳性”安慰剂作用的因素也有可能引起不利影响,称为Nocebo效应。“我的同事将诺斯博(Nocebo)称为邪恶的双胞胎,但我将其视为堂兄,” Kaptchuk说。“在随机对照试验中,无论您在活跃的药物臂中观察到什么副作用(除了一些例外),您将在安慰剂组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效果。您不会在安慰剂臂中遇到的一些事件,但是在两者中都会出现疲劳,头痛,恶心,头晕,不适,成就等常见症状。”
Kaptchuk指出了可能发生Nocebo效应的各种原因,例如,这可能是由于安慰剂,但也可能是由于错误贡献。他详细阐述:“一个人可能会感到定期头痛,例如,他们开始服用新药,并且会头疼。他们不会认为这是他们通常的头痛之一,他们会认为这是从毒品中的。”
As highlighted by Kaptchuk, individuals could be attributing side effects to drugs that are actually caused by anticipation of negative effects or heightened attentiveness to “normal” day-to-day discomforts: “It's background noise that gets interpreted as placebo, that’s why nocebo effects are very large.”
根据Kaptchuk的说法,在Nocebo方面的另一个关键考虑是机制。“这并不是患者期望变得更好;我们从我的团队进行的神经影像学研究中知道这一点,这些研究已由其他研究团队复制。取而代之的是,当您查看大脑中的Nocebo效应并评估该现象的参与时,它包括海马,从未发生过安慰剂作用。”
“海马在焦虑中参与了焦虑,焦虑可能表现为头痛,皮疹等。但是,对于研究研究中的任何个人,在双盲临床试验中涉及Nocebo效应时,大多数Nocebo效应活性药物的作用感觉相同。使用好的药物,Nocebo效应小于该药物的组效应。Nocebo和安慰剂作用感觉与药物相同。”
“我的同事将诺斯博(Nocebo)称为邪恶的双胞胎,但我将其视为堂兄,”
2022年1月,Kaptchuk和团队published调查结果JAMA网络开放关于随机和安慰剂对照的Covid-19疫苗试验中的Nocebo效应。这研究人员比较在12个出版物的安慰剂和疫苗组中,不良事件的发生率(AES)总共有45,380个试验参与者(22,578个安慰剂接受者和22,802名疫苗接收者)。
Systemic AEs were reported by 35% of participants after receiving their first dose of a placebo, with headache (19.6%) and fatigue (16.7%) most commonly reported as minor symptoms. Local AEs (e.g., pain or swelling at the site of administration) were reported in 16.7% of those receiving placebo.
46%的接受疫苗的参与者经历了一种系统性AE。第二剂安慰剂后,有32%的参与者报告了全身性AE,有12%的参与者报告了局部AE。对于接受Covid-19疫苗的人,有61%的人报告了第二次剂量后的全身性AE,而73%的人报告了局部AE。
基于这些数字,研究人员认为,在第一次剂量后,有76%的全身性AE和第二剂剂量后的全身性AE的52%实际上是Nocebo的反应。
Kaptchuk说:“对于19009疫苗组中的每100个副作用,安慰剂组中都有76个相同的副作用,这意味着许多这些副作用实际上是Nocebo的反应。”他指出,尽管他们能够识别出Nocebo的反应,但他们无法确定这些影响是否是焦虑的结果or由于错误贡献。
安慰剂效果和贝叶斯大脑
“我在安慰剂研究中的大多数同事都说安慰剂效应是由期望引起的。您期望变得更好,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您会变得更好。那是当您对健康正常的欺骗性实验时,是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期望是否会在临床人群中产生安慰剂作用的证据仅限于精神病学领域的一两个实验。”他说。
Kaptchuk解释了心灵的问题-身体概念是,没有明显的途径从头脑到身体,反之亦然。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神经递质和遗传学在安慰剂反应中起作用,但确切的过程仍然难以捉摸。“在某些时候有些人在某些人的背部服用安慰剂药可以减轻背部的缓解?”他问。
一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与安慰剂治疗的机制有关,该机制与中心敏化有关,意思是,它们不会摆脱硬病理生理学,它们摆脱了神经系统的扩增。
Kaptchuk承认:“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想法,尽管上面写了几篇论文,但并不容易解释。”为了解释理论,他分享了一个场景:“一个人经历了三个星期的背痛-扭伤了。但是那伤害应该治愈...除了没有他们继续感到痛苦。病人拜访了多个医生,他们被告知“一切都在您的脑海中!”。被告知没有生物学的理由会导致疼痛使它们变得更好,如果有的话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这个人的痛苦不是不是real, they are experiencing pain – it’s just that places in their somatic cortex are hypersensitive despite the original physical injury being healed, which according to Kaptchuk, is why doctors are unable to find underlying pathophysiology or “root cause” of the pain.
“自下而上的症状感知背痛,尤其是其不健康的放大,发生通过涉及中枢致敏的神经分布系统(神经超敏反应),而对于慢性疼痛,则会产生对症状的感知,有时是严重的,没有疾病,在腰部。”
Kaptchuk继续说:“患者正在经历的放大具有非常清晰的理论模型,称为贝叶斯大脑预测编码,” Kaptchuk说。“当您给安慰剂时,您实际上会拒绝放大一些人们一些的时间。引起扩增的途径与安慰剂使用的途径相同。”
当一个人感觉到从糖粉中改善背部的症状时,相同的贝叶斯系统正在运行,但朝相反的方向运行,有时会自动导致大脑减轻疼痛的感觉。
根据Kaptchuk的说法,这与症状应用处理有关。“贝叶斯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这与大脑计算的方式有关-这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how Bayesian models offer a different picture of how the brain perceives symptoms and relief, Kaptchuk highlights two recent publications in疼痛andBMJ。
Realizing the power of placebo
Kaptchuk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对似乎具有潜在价值的治疗方式有偏见,偏见?透明
He provides me with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his point: “In 1095, Pope Urban II declared that Jewish doctors were not allowed to touch Christian patients or see them. And it wasn’t because they weren't good doctors – in fact his自己的doctor was secretly a Jewish doctor-这是因为当时他们认为这是魔鬼的工作。您在这里拥有的是一种康复的方式,但是您可以说,这是生物医学魔鬼的工作。”
从我们的谈话中,我相信,这是Kaptchuk的多学科职业和替代医学的经验,使他能够看到安慰剂效应的潜力以外的人,从而使他成为该领域的领导者。
He closes our interview by saying,
“我多年来一直是安慰剂的学生,我与之搏斗,但我知道那里有些东西,我的工作最终将其从边缘带到医学和治愈的中心问题。”
Ted J. Kaptchuk教授was speaking with Laura Elizabeth Lansdowne, Managing Editor at Technology Networks.



